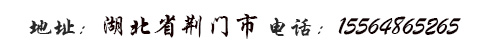和人性的疯癫对话我在美国精神病院实习的日
|
儿童白癜风怎样治疗 http://pf.39.net/bdfyy/qsnbdf/ 和人性的疯癫对话: 我在美国精神病院实习的日子 文 文岚 点击??收听来自南京上空最温柔的声音 文岚的话 与春媚结识是在去年一个秋雨绵绵的下午,去中山陵半山腰一个叫做永慕庐的地方,参加郭海平老师关于他原生艺术拓荒之旅的一个讲座,环境很安谧、因为下着雨更觉着与喧嚣世界的隔绝感,讲座很精彩,同时,我也结识了讲座的女主持,一个来自美国西肯塔基州立大学的历史系副教授,也是美国国家认证的心理咨询师,我对她的后一个身份更感兴趣,当时她在南大做交流学者。 最初接触,我看到的是春媚的专业、美丽,后来在生活中逐渐熟悉,我看到了她在她生命的这个特殊阶段抹不去的疲惫、伤感、后来还看到了她对现代舞的执着热情,在她离开南京时,我也体会到她对我当时心境的安抚、感受到了她对朋友饱满的爱。我有在内心为收获到这个独特而美丽的朋友窃喜。今年七月春媚离开南京回美国之前,我收到了她的这本刚出炉的新书。 在美国任职历史系副教授的同时,春媚修读心理咨询课程,进入一家精神病院实习。她管这所精神病院叫“伤河”,在这里,她体会病人的悲苦,也等待自己的重生。基于这段经历,她写下非虚构作品《疯癫笔记:我在美国精神病院的实习经历》。 不知你是否与我一样对人性有执着的热情,对特殊人群的灵魂有一份强烈的探寻之心,希望走过一座桥,打破一层隔膜,便走进人性的团圆和温暖。 今天,我要为你读春媚的新书中的一部分,我们要跟着春媚的笔触,走进一片特别的领地。 伤河:我在美国精神病院实习 文 春媚 年夏天,我在异乡独自面对陌生的人群。正常与非常、疯癫与理性、病态与常态之间究竟有怎样的界限?一直研究历史变迁的我,这次试图进入个人的私密空间,直面伤痛。 此时的我已博士毕业,在美国高校的历史系执教多年;之前两年多里又修完了心理咨询课,再完成小时临床实习后便可以获得专业硕士学位。此时距离L的离去也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很想给这一段人生画上一个句号,但也许是一个逗号或者是冒号。 我写下笔记,纪念接触过的所有病人的悲苦。同时,故事也发生在我身处个人危机的旋涡时绝望的疗伤中。也许这是我一次“参与观察”的人类学尝试,一个对L逝去的纪念,不过它更是我发现情感与探求精神的旅程,也许我的使命就是做一个荣格所说的“受伤的治愈者”。 带着自己的秘密,我站在人生的分水岭,既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又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我管这家精神病院叫“伤河”。它是一座四处平铺开来的灰色单层建筑,和普通学校并无二致。这家医院位于美国中西部小镇上,接收急性和慢性病人,主要来自邻近的两三个州。医院有一百多个床位,分六个病室: 他们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是自残、性侵、暴力、吸毒、酗酒、抑郁、躁狂、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因丧失而孤独,因绝望而欺骗,因思念而自责,因痛苦而恐惧,因渴望而疯癫,这与我们并无二异。 更多的时候,我震惊于每天的所闻所见:他们不是常青藤、华尔街、硅谷的美国,也不是美国梦的美国;他们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美国,是让人理解川普当选的美国,是不为人知但更为真实的美国。 精神病院“伤河”位于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 乍一看像所学校。 我的工作从名曰“十字路口”的戒瘾科室开始,它专门接收毒品和酒精治疗的成年病人,其中很多人都有或多或少的犯罪历史,大多和吸毒、贩毒、携毒、盗窃、酒驾相关。 有人被法官勒令戒毒,以免牢狱之灾,运气差的出院后仍要直奔监牢。并不是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地待在这里,诚心悔过只是天真的想象。我在这里见识了众多智勇双全的厉害角色。 最初我对酗酒吸毒还知之甚少。它是一种疾病,和先天遗传有所关联,并不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过我脑中更多浮现的还是电影和新闻中吸毒、犯罪、艾滋病的种种画面。就在这种对禁忌和绝症的恐惧和好奇中,我开始了在精神病院的工作。 作者MisleidysCastillo,作品名《E》。 周三下午一点半,我带着笔记本和讲义准时来到多功能室,黑色夹克和长裤尽力武装出专业。房间里有一台电视,新添的三张长沙发,再加上十几张舒适的靠背椅,都是功能性的家具,没有一丝无用的奢华。 正对着座位的黑板上画着成瘾的趋向图,墙上是24小时的时刻表。靠墙的窗户是双面玻璃窗:外面可以看清里面的一举一动,从里向外看却只是面镜子。多功能室的另一扇门正对着护士办公室,那是信息的主要渠道,每天都在传播世间离奇的故事。 早上八点半,晨烟缭绕的每日例会。“四月的情绪很不稳定,会很麻烦。”咨询师B说道,她刚给四月做了入院的心理评估。B是一个有着三十年经验的老咨询师,熟悉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被阅人无数的她称为麻烦的女人会是什么样子呢? 精神科医生M拿起一本病历,书脊上写着四月的全名。“五十四岁,离异,有长期过度服用止痛药的历史。抑郁症和毒品依赖,自愿求助,低收入人群医保,”B一边简单明了介绍,一边在文件上迅速勾画出无数个签名。 作者DamiánValdésDilla,作品名《无标题》。 这间小型会议室原是一间病房,正对着进出“十字路口”科室的走廊,可以看见病人列队去吃早饭,排一行长队,点名后跟随工作人员鱼贯而出。他们通常安静而散漫。 穿背心人字拖的男人,背后的纹身呼之欲出,玫瑰花、美洲豹、十字架,突兀的光头好似某种现代艺术的景观。身着睡衣的女人,未干的长发散落在身后,好似刚从台风中被抢救出来的幸存者,又如马戏团里正在表演的海豹,拖着肿胀的小腿缓慢滑行。 眼前的这支队伍奇奇怪怪,不伦不类。他们有一早下楼买油条般的随意,又夹杂着一股说不出来的气。这股气有时是桃红色的,他们大声地说着某种笑话,粗暴地笑;有时变成深紫色的埋怨和各种有理无理的要求;有时候又变成了很淡的灰白色,很轻很轻,几乎没有声响地飘过,不留任何痕迹。这里有怒气、怨气、戾气,还有哀气和丧气。 作者CandiceJ.Avery,作品分别为《笼中事物》(左)与《经济崩溃》(右)。 “又是一个药物沉溺的老年妇女,加上个人创伤史。”M翻看着四月的病历。止痛药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药物沉溺的来源。药品变毒品的路程并不复杂,很多人因为疼痛而服药,不幸上瘾,然后打着药物的名头,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并非瘾君子,只是为疾病继续服用。 长期使用止痛药可能导致药物成瘾——?一种不计后果持续服药的强迫行为。当身体适应药物的存在,突然停止,就会产生戒断症状,好像长期酗酒抽烟的人突然戒掉之后的烦躁痉挛、呕吐腹泻、失眠疼痛等。于是很多人装病以获得处方药物,再有就是在黑市上购买,后来又转向海洛因作为替代品;没有办法时,也有人就着药店里的非处方咳嗽药成瓶灌下去,以获得些许缓解。 夏日午后,方才还是骄阳似火,顷刻间就大雨瓢泼。停车场上偶尔有驶出驶进的车辆,大多是换岗的护士。值晚班的护士下午四点上班、午夜下班,此时她们正带着异于常人的振奋在雨中阔步前行。 四月踩着这股局促的水汽走了进来。个子很小,只有一米五,语速飞快,音调很低,有着抽烟或者哭泣之后扁平沙哑的音色。她既不年轻,也不显老,一种并非故意隐藏的难以判断。她穿着牛仔裤加短袖T恤的标配,外面还罩着长袖格子衬衫。五十岁后的妇女大多已经明白了装嫩的虚妄,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年轻穿在外面。 “我该怎么办呢?”四月露出第一天上学似的忐忑不安,又有生怕做错事被罚般的小心翼翼。她说话时紧盯着你,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漏掉至关紧要的信息。和这里大多数病人不同,她满心都是想要留下的绝望。 ““我是你的咨询师,今天第一次单独见面,医院求助的原因。” “我再也撑不下去了。只有我和娜娜。娜娜走了,我每天守在她的床边,她是我唯一的希望。四年了,我每天都去她的墓前。一年前,我的祖母也走了。六年前,丈夫死了……” ”被父母遗弃的四月从小由祖母养大,二十几岁时嫁给了一个大她十六岁的男人。两人非常恩爱,女儿的到来更是增添了无数欢乐,直到丈夫去世,直到女儿离开。四月独白式的哭诉持续了十多分钟,她的情绪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并不是我技艺高超,而是她积郁太久,到了无法不说的地步。任何人此时坐在对面,她都会毫无保留地倾诉吧。 ““你这一路走来,一定很难。”良好的信任关系是心理治疗成败的关键,我循规继续,可是内心的不安已如潮水般涌起。 “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嗑药的。太难熬了,冬天的夜晚,没有人听我倾诉,没有人理解我。” “马丁呢?”马丁是四月的男朋友,他们住在一起。 “他是个农民,你知道的。是个好人,可他并不关心这些事情。他有自己的儿女,并不懂得我的痛苦。”四月刚刚停止的哭泣又开始了,甚至更加猛烈。“也许娜娜本不该死的,也许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你认为自己要对女儿的死负责。”我想让四月看到这是她选择并强加给自己的观点,而非铁的事实。 “我们那时没有医疗保险,如果我有钱的话……”四月继续以一种在法庭受审的口吻喃喃念叨着。 ”娜娜生病后,四月辞去了干了三十年的老年护理工作,专心照顾女儿,也丢了收入。娜娜的死因,我当时并不知晓,直到两周后某一天她嚎啕大哭泄露了女儿最后时刻的惨状,全身流血是由于吸毒造成的内脏功能衰竭。 少者去而长者存,世上的痛莫大于此吧。在毒品中寻找解脱的她,面对杀死女儿的凶手自己也无法自拔,日日受自我谴责的折磨。可是谁又不会自责呢?“如果”的问题谁又没有千百次地追问过自己?死亡是最不理性的事实,对存在的终极挑战。 作者BorisSantamaría,作品名《无标题》。 我瞄了一眼墙上的钟摆,半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是只能紧盯着她的脖颈,做出直视的假象。丧失之痛,也许会越来越容易,但是永远不会变轻。 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场,只有将电波调到与咨询者同一个频率时,才能与她接轨。所谓共情,就是她在哪里,我就去哪里,无论是在她没有准备好时陪在谷底,还是等她有了点气力时一同攀岩并提醒她陷阱。 只有在绝对的真实和支持前,病人才能放下种种的畏惧和禁锢。于是两个赤裸裸的灵魂,在最深处建立了某种联系;双方共同走过一段艰苦的旅程,说是情感和精神的伴侣也不为过。就在这样的交互中,心灵的治愈神奇地发生,双方都有一种不可言说但心领神会的感受。 接下来几周,四月有所好转。我们还是在谈娜娜,有了我这个听众,另一个知道娜娜存在的人,四月似乎不那么孤单,少了些绝望,情绪也稳定下来。身体里的毒素排除之后,她开始有了笑容,愿意分享,并且还帮助其他病友。 体内那份爱人的天性,在许久的沉寂之后喷涌而出,终于又找到了抒发的对象,甚至惹得同屋妮娜颇有怨言:她让我不要在餐厅里说话,她叫我多收拾房间少喝可乐,她把我当成了女儿对待! 可是有一天四月突然反复,像断线的风筝。她第一次在面谈时没有哭泣。 ““昨天我和马克通电话了,”她埋着头,没有看我,“我们吵了一架。” “为什么?你不是说他很支持你的治疗吗?” “昨天我们谈到娜娜的东西,马克问我什么时候把它们处理掉。”娜娜去世四年了,四月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她的物品。如今搬到马克的农场上住,娜娜的东西也跟着过来,占据了一整间的地方。 “我答应过他会处理,但现在不行,我还没有准备好。我求他给我点时间,千万不要碰它们,一切等我回去了再说。”四月的绝望弥漫在入秋的夜气里。 “所有的亲人都遗弃了我,母亲根本不在乎娜娜的死,葬礼那天,她都没有来。”这是四月第一次提到母亲。我想起她的病历:父亲早亡,遭母亲遗弃,祖母抚养成人。“再没有人了,我是世上唯一记得娜娜的人。我要留住娜娜,不会让任何人把她磨灭的。如果我也死了,那么一切就真的结束了。” “我的世界里只有娜娜,她死后,一部分的我也死了。” ”延续娜娜的存在是支撑四月度过无数个孤独痛苦的夜晚的力量。四月告别的不仅是娜娜,更是她自己的过去和幻想。娜娜是女儿,也是四月实现完整家庭、幸福童年的希望。四月挽救不了娜娜,娜娜也无法成为四月的救赎;四月需要重新找到自己。 作者CandiceJ.Avery,作品名《披头士》。本画作及以下精神病人画作由美国一家非盈利机构NAEMI提供并授权作者使用。NAEMI的全称是美国精神疾患艺术展览组织,于年专为支持和传播患有精神疾病者的诗歌、绘画等艺术创作而成立。 ·END· 原创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uihaibaoa.com/hhbfzfs/6374.html
- 上一篇文章: 男生在啪啪啪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
- 下一篇文章: 对比版山东春考英语年考试大纲与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