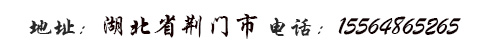哈代黑暗中的鸫鸟
|
白癜风的发病原因有哪些 http://baidianfeng.39.net/bdfby/yqyy/ 托马斯·哈代ThomasHardy - 飞白译托马斯·哈代 诗十首 黑暗中的鸫鸟 年12月31日 我倚在以树丛作篱的门边, 寒霜像幽灵般发灰, 冬的沉渣使那白日之眼 在苍白中更添憔悴。 纠缠的藤蔓在天上划线, 宛如断了的琴弦, 而出没附近的一切人类 都已退到家中火边。 陆地轮廓分明,望去恰似 斜卧着世纪的尸体, 阴沉的天穹是他的墓室, 风在为他哀悼哭泣。 自古以来萌芽生长的冲动 已收缩得又干又硬, 大地上每个灵魂与我一同 似乎都已丧失热情。 突然间,头顶上有个声音 在细枝萧瑟间升起, 一曲黄昏之歌满腔热情 唱出了无限欣喜,—— 这是一只鸫鸟,瘦弱、老衰, 羽毛被阵风吹乱, 却决心把它的心灵敞开, 倾泻向浓浓的黑暗。 远远近近,任你四处寻找, 在地面的万物上 值得欢唱的原因是那么少, 是什么使它欣喜若狂? 这使我觉得:它颤音的歌词, 它欢乐曲晚安曲调 含有某种幸福希望——为它所知 而不为我所晓。 声音 我思念的女人,我听见你的声音, 一声声地把我呼唤,呼唤, 说你现在不再是与我疏远的模样, 又复是当初我们幸福的容颜。 真是你的声音吗?那么让我看看你, 站着,就象当年等我在镇边, 象你惯常那样站着:我熟悉的身姿, 与众不同的连衣裙,一身天蓝! 也许,这不过是微风朝我这边吹来, 懒洋洋地拂过湿润的草地, 而你已永远化为无知觉的空白, 无论远近,我再也听不到你? 我的周围落叶纷纷, 我迎向前,步履蹒跚。 透过荆棘丛渗过来稀薄的北风, 送来一个女人的呼唤。 以后 当“现在”在我不安的逗留告终时闩上了后门, 当五月扑动欢乐的绿叶像鸟儿鼓翅。 片片都覆盖着精细的膜如同蛛丝,邻居们 会不会说;“他平素爱注意这样的事?” 如果在暮色里.夜隼随着寒露悄悄下降, 穿过暗影飞来,像眨眼般无声无息, 落在被风压弯的山地荆棘上,凝视者会想: “对于他,这景象该是多么熟悉。” 如果我消逝于夜蛾飞舞的温暖的黑夜, 当那刺猬小心翼翼地漫游草地, 有人会说:“他力求使这些无辜生物不受迫害, 但他也无能为力;而如今他已离去。” 如果听得我最终归于沉默.人们站在门口 凝望着冬夜缀满天空的星斗辉煌, 永远告别了我的人们,会不会浮起一个念头 “他最善于欣赏这样的神奇景象?” 当暮色苍茫中响起我离去的钟声,它的嗡鸣 被逆风切断而暂止,待到再响之时, 拾似另一口新钟,这时会不会有人说:“他如今 听不见了,但他平素爱捕捉细微的事?” 对镜 当我照我的镜, 见我形容憔悴, 我说:“但愿上天让我的心 也像这样凋萎!” 那时,人心对我变冷, 我再也不忧戚, 我将能孤独而平静, 等待永久的安息。 可叹时间偷走一半, 却让一半留存, 被时间摇撼的黄昏之躯中 搏动着正午的心。 伤口 我爬上山的顶端, 见西天尘雾蒙蒙, 太阳躺在其间, 恰似伤口的血红。 恰如我的伤口, 谁也不会知晓, 因我不曾袒露 心被刺透的记号。 最后的情话 这是最后的情话;最后的情话! 从此,一切都默然死寂, 只有苍白的裹尸布罩着过去, 它在那时, 爱人啊,对我不会具有 任何价值! 我不能再说;我已经说得太多。 我不是指它一定来临; 我不知道它会这般增强-- 或许也未弄明 你的第一个抚摸和目光 注定了我俩的命运! 沉思的少女 “默默无闻的人儿,你为何经常 独自一人悄悄地溜开?” 她猛吃一惊,微微掉头, 满面羞色地说了起来: “每当风标指向他那遥远的故乡, 我就登上陡峭的山坡, 我想吹拂过他嘴唇的微风, 此刻也会在我唇边抚摸。 “每当他披着晚霞散步, 我就倘佯到白色的大路, 心中甜蜜地沉思冥想: 这条路会连接他的脚步。 “每当驳船向伦敦航行, 我观看着它们在远处消逝; 他的窗口正朝着码头, 驳船的来临他能尽收眼底。 “我去迎接夜空中的明月; 赏月给我们带来了满足; 只要他还有着昔日的情趣, 我们的目光就能在夜空任意撞触。” 旅行之后 我来到此地,看一个无声的鬼魂, 它的狂想要把我引向何处? 上悬崖,下峭壁,直到我茫然孤零, 看不见的泉水的喷涌使我恐惧。 不知道你接着将在哪里藏身, 但到处都会在我眼前呈现 你栗色的发,灰色的眼, 还有时显时隐的玫瑰色的红晕。 是呵,我终于重访你昔日常游的地方, 跟随你跨过岁月和消逝的美景; 朝着你把我抛下的黑色空间凝望, 对于我们的过去你想说些什么事情? 夏日给了我们甜蜜,秋天却带来了分离? 还是想说我们两人 晚年不如初期幸运? 但任凭时光嘲弄,一切都已终止。 我看见你的干什么:你正领我前往 我俩在此逗留时熟知的地点, 在那晴朗的天气,美妙的时光, 来到身披云雾彩虹的瀑布旁边, 还有底下的洞穴,传来依旧瓮隆的声音, 仿佛四十年前一个声音把我呼唤, 那时你是生气勃然, 而不是我如今茫然追踪的虚幻的幽灵! 晨鸟用嘴梳理羽毛,海豹懒懒地扑腾, 它们看不见什么东西在此飘忽, 亲人呵,你很快就要从我身边融消, 因为繁星已关门窗,黎明已拉开天幕, 相信我吧,虽说人生阴沉,我却不在意 你把我引向这里。愿你再领我到这个地方! 我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 那时我们的道路铺满鲜花,生活充满乐趣。 偶然 但求有个复仇之神从天上喊我, 并且大笑着说;“受苦受难的东西! 要明白你的哀戚正是我的娱乐, 你的爱之亏损正是我的恨之盈利!” 那时啊,我将默然忍受,坚持至死, 在不公正的神谴之下心如铁石; 同时又因我所流的全部眼泪 均由比我更强者判定,而稍感宽慰。 可惜并无此事。为什么欢乐被杀戮, 为什么播下的美好希望从未实现? ——是纯粹的偶然遮住了阳光雨露, 掷子的时运不掷欢欣却掷出悲叹…… 这些盲目的裁判本来能在我的旅途 播撒幸福,并不比播撒痛苦更难。 曲终 我们莫再迷恋 这又甜又苦的游戏,—— 爱情之光最后一次 闪耀在你我之间。 我俩紧密的联系 将不留踪迹地消失, 我俩约会的地址 将恢复早先的孤寂。 百花和香草的熏风 是否会把我们思念? 野蜂不见我们留连, 是否会压低嗡鸣? 尽管我们盟誓热烈, 尽管欢乐如泉水涌出, 幸福达到了它的限度, 如今看到了最后判决。 深深地痛,但不呻吟, 出声地笑,无声地受苦,—— 爱之路比那石头路 要更为崎岖难行。 威斯坦·休·奥登WystanHughAudn – 叶美译威斯坦·休·奥登 文学转变 我不能客观地评价托马斯·哈代,因为我曾深爱过他。 十六岁之前我没读过一首诗,我成长于一个偏重科学知识的家庭,文学氛围不浓厚,我是由铅矿,窄轨电车和水车组成的梦幻乡村里唯一的异类。但年三月,我决定成为一名诗人,接下来的十二个月里我扫荡了学校图书馆,没几周就换一个诗人读,德拉·梅尔,W.H.戴维斯,甚至阿尔弗莱德·爱德华·霍斯曼,却都没有找到我想要的。 我尚未遇到一位三十岁以下的诗歌爱好者,他不能是那种性格内向的人,或内向可以,但不能有一个不快乐的青春期。特别是,如果,拿我自己举例子来说,上的是一个寄宿学校,他看见性格外向的人才受欢迎,能给人幸福感,乐善好施,他自己则不得人心和被忽略,但最不能忍受的不是不受欢迎,而是认为自己确实自作自受,自己卑鄙,低人一等,笨拙又胆小怕事。一旦想根本没有人和自己志趣相投时,竟确信这就是事物的正常秩序,自己命中注定会有一个充满失败和嫉妒的人生。直到他长大后的某天,直到多年之后偶尔遇见校园时代的那些偶像们,发现他们其实如此苍白,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了。终于他相信内向的性格是笔大财富,最适合在工业文明里生存,因为工业文明的集体价值观如此幼稚,以至于他可以独自成长,还培养了自己的幻想能力并学习怎样汲取内在生命资源。但那时他的青春期过得实在苦闷,根本不能想象出会有个社会可以身处其中并感觉自由自在,也被来自神秘的本能心存芥蒂,曾经他为寻求安慰而让记忆回闪到童年那些高不可攀或可怕的人物,这条路同样行不通,所以他从人类出走,走向人类之外:他患上了怀乡病,但他找寻的不是自己母亲,而是大山,秋天的森林,孤苦无依地静观野蛮动物害羞的一面,他心中不断增长的生命体验决心要对音乐无限忠诚,同时思考起人世沧桑和死亡来。艺术对他来说无限珍贵,艺术悲观厌世,并与生命敌对。如果它谈论爱,那也是受挫败的爱,因为成功在他眼里都哗众取宠,庸俗无比;如果它说教,它必须给出建议是坚韧地服从,因为他所知道的世界从来都是自行其是,不会改变。 初恋时一往情深,激动无可挽回 啊,生命中的死亡,使日子没有未来 而现在,死更是多么的富丽 在午夜里可燃魂离人间 [查良铮译] 死人永远不能再起 甚至最缓慢的河溪,也会安然盘旋到海里 [梁实秋译] 情人们彼此依偎着对方 不要问在旁入睡的是哪位 新郎整夜不睡 要把新娘交还 上面的诗句对于处于青春期的人来说就是诗歌的真实典范,无论是丁尼生、济慈、斯温伯格、霍斯曼或其他人,无论在他的生命中第一次被其中哪一位诗人打动,都会激起一种模仿的激情,而后来岁月中他的诗歌品味会左右不离其中。我自己这方面深受影响的人物是年夏天的哈代,有一年之久我谁都不读,不用费力去回忆我就知道我读的是那漂亮精装的维塞克斯版本:我把它们私运到班级里,星期天散步也随身携带,回寝室也带上以便在清晨读上两页,尽管放到床上太笨重了些。后来年秋天发生了宫廷政变,我必须在我的哈代王国里放入爱德华·托马斯,再后来他俩在年的牛津战役中被艾略特双双打败。 除了是我心目中诗人的典范,哈代的诗歌还有对时代的展现,他是我心目中济慈和卡尔·桑德堡的化身。 从第一眼,他看起来就像是我的父亲:浓密张扬的胡须,前额明亮,脸皱纹深厚,和善,那是能感知和思考另一个世界的脸,(而我,和我母亲一样,是个凭直觉思考的人),我知道他是这样一位作家,如果说他在表达的时候,有时显得单调和多愁善感,那是因为他的情感比我自己更加深刻和忠诚,对世界的爱比我更坚固,严格。 女幽灵骑手。他虽然,辛苦尝试着寻找 每日都陷入心灰意冷 因为她在时间不能所及之处 但她能,仍能欢唱地骑行于 他一心入迷的思想里 骑行于粗犷,泥质的 大西洋区域 他望向她第一眼时 她拉住缰绳,正对着荡漾的潮汐哼唱 (《女幽灵骑手》) 不会有山峰,树木,尖塔的阴影 当世界一无改变时 落在我的坟墓上,也不会片刻之后 悄悄移步你那 从没有一只知更鸟停留在我们头顶绿色的植被上。 (《生离死别》) 《重游旧地寻时光》中的许多诗都深深打动了我,不仅因为感同身受的原因——我当时正在爱情中失意——也因为我有点怀疑我自己的个性相反,是个极端冷酷又善变的人,我羡慕那些易感动的人。 还有一点,哈代诗歌中的世界就是我自己的童年世界:它淳朴守旧,它是道德统一的英格兰,有牧师,医生,律师,建筑师,它是有着维多利亚色彩的英格兰,人们一星期去教堂两次,每日早餐前做家庭祈祷,没机会结识离婚的人和骗子,出门用的是装饰圆铜和古董的轻便马车或自行车,以家庭为中心搞些娱乐活动,开朗诵会,搞园艺,散步,钢琴二重奏和玩哑语字谜游戏,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对伦敦,政界或法国文学置身事外的英格兰。 学校有几个伦敦人,这些拿腔拿调的优雅家伙们——其中一个据说为了享乐才读莱辛。现在回头去看,我觉得多么幸运,当时的腼腆,不善交际,没有机会结识和模仿他们,因为他们喜欢的作家不一定适合我,会危险地鼓动我假装去喜欢一种和我自己个人经历没有关系的人生。过早地进行抽象思维和接触“现代”作家危险太多,得不偿失,在当代任何学术科目上,我已经看到太多中毒较深的例子。我找到了哈代这个正好写我自己世界的诗人,是多么幸运,我或许会很容易地着迷乔治王时代的一个或某个人,但肯定所学甚少,因为他们都是伦敦人,脱离自身观察世界。 因此我,蹒跚向前 树叶环绕我缓缓降落 从东面吹过的微风穿过荆棘 此时有女士在呼喊。 冰柱引领教堂过道向前 旗绳急切不安嘶哑地说着 家园的脚步声包裹它们落满碎雪的头- 但我仍然追踪它的进程 我们中的一个……黑皮肤,性格耿直的他,黑皮肤性格耿直的她,离世了 其他人,不久也消失了 但是上帝知道,如果他什么都知道,我爱上了古老的一百年的他,圣斯蒂芬的 子恩山,安息日的日子,车道,神圣的宁静,阿拉伯半岛和伊顿 我到达大理石般的乡村 呼吸声越过空气 如海盐般明亮 我看见了人世沧桑和潮起潮落 当她就在那里 所有国家的船往来这里 奴隶在阳光下迅速交易 跳动的华尔兹 女学生们沿着草粑在大笑 她就是其中的一个。 所有这些都是我自己生命经验的一部分,所以我能够感同身受,因它们古老的色彩,我才得以理解,但又足够现代使我受益匪浅。 哈代出生在一个农业社会,一个没有被工业和城市价值碰触的社会,当他去世时这个社会模式已经瓦解了。对丁尼生一直困惑的科学和信仰的冲突问题,也一样折磨着哈代,但是哈代应该活得更长久一些才好,以至能超出丁尼生的和解态度。叔本华的悲观,斯宾诺莎的宿命论当然不是解决之道,但它们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必经阶段,逃也逃不掉,人们总是活在具体的境遇里。 哈代是个有创造力的诗人,对我而言不简单地是个保姆型的人,不是我一旦长大自认成熟后就可以抛到脑后的诗人。我们时代的问题很多都是个性发展的问题。敌人要摧毁我们的忠诚和信仰,维多利亚人当时所谓的宗教真理和科学真理之间的矛盾冲突现在已更名为个人和整体,有意识的自我和无意识身份,意愿或确定,也就是这方面使哈代的诗歌更独特,价值长久。维多利亚那一代人都是自信的个人主义者,仅仅因为世界和传统的共同关系纽带是强壮的。我们自己这一代出生太晚了以至于即没机会接续传统,又不幸地失却了个人解放的激情:因此我们太容易陷入集体主义的病态崇拜。 话说回来,在哈代身上我最看重的,我现在也仍然坚持的是他锐利的眼光,他看待生命的方式老道,就像诗剧《列王》的舞台提示和《还乡》的第一章所写的。把人的生命不仅看成是和此时此刻的社会生活相关,也和整个人类历史,生命,星空相关,人类既谦逊又自负。从这个观点看个人和社会的矛盾是如此轻微,因为两者都微不足道,以至后者应该停止自己作为一个有绝对权威万能神的角色,而是地位与人类平等,共同服从一个繁荣凋零的法规,因此和解是可能的。 拥有此世界观的人不会同时是一个以自我中心的,超理性的人道主义,它要求高度自由地想象我们自己的生命,又同时是一个伪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反对个人的自由意志,但却声称人类社会可以自动更新,不受控制地向前发展。 是哈代教会了我区分艾洛斯和逻各斯的关系。 啊,你不知道她的秘密所在吗,她自负隐藏缺点吗 她那些伤害自己钟爱生命的不明智之举从何而来吗? 最轻微的是她的那些运转轨迹?——它们阻止它信仰上帝 带来那些可怕的未竟事业,那些通过她区域的红色避难所 所有的造物因何咆哮呢 那时,他的暗中摸索的技能,没有蔑视,没有咒骂 不久将会压住她的手,那只专伤害它所爱的事物的手 当她缓慢地行走沉思着死亡,在痛苦的黑暗之中 无论怎样你帮助她 不久她会消失。 对这个问题,“逻各斯——意识由意志的形成,直到它平等地塑造所有万物——从哪里来?它是施舍给我们的恩泽还是被艾洛斯所创造的呢?”哈代没有回答。在理论上可能他思考像希腊人,说是意识能够扭转意志。今天这说法是令人怀疑的,因为神秘的直觉自始就有并存在,并且真如此的话——这么说是因为机器把艾洛斯从古老的永恒规则中解放出来,那么,公开有计划地苦行并且严于律己才是解决我们混乱和受压抑之痛苦最好的道路。如此以来,我们可以向我们自己也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哈代和其他人使我们看到了它的存在。 哈代给当时少年的我提供了很多帮助,扩展了我的视野,但我欠他在另外一些方面,对我个人来讲,一笔更重要的债,是关于技术上的指导。再次我想在选择上我是极端幸运的。首先,从一开始哈代的缺陷作为一名手艺人,他节奏上的笨拙,他的古怪的词汇甚至对中学生都是明显的,而一名年轻人恰恰是可以很好地从中学到些什么,因为他们可以评价这些诗。莎士比亚和什么权威大师们使人炫目又失去信心。第二个方面是没有一个英国诗人,甚至包括多恩和勃朗宁,开发出如此多的,如此复杂的诗节。任何人想要模仿他的风格至少需要学会一样,那就是怎样制造词语,去适合复杂的结构,同时如果他是对这些事情敏感的,就会特别关于形式决定内容这件事。 沿着比尔山 岛上,很多人居住着—— 那像众多雕塑般的,秃头,皱眉的脸—— 深渊和沉寂精神一直在我身上 热血沸腾,我活着,持续地 这种不同寻常的诗歌形式有助于帮助模仿者发现他想要说的是什么:传统的形式像十四行诗在思想和态度上有一套一成不变的定式,不成熟的模仿者根本没有办法。另一方面模仿者认为写的自由诗看起来容易,实际上未必如此,而是得面对巨大的困难,只有那些在表达意图和能力浑然一体的人才能够权驾得了,那些把自己的写作限制在自由诗这种形式的人,因为他们认为形式的不自由必然会导致内容的不真,他们不理解艺术的本质,认为若艺术家事先按形式有意识地写作,作品就会毫无价值,并认为语言之所以最有力量,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偶然性。 哈代从这方面解救了我,另外教会我诗歌直接的口语用语,重点在句子,字节上的影响,而不是意象。 我已看见你干了什么,你正在引导我…… 那些岸边我们完全忘了的绅士们 你就是经常注意这些事的这么个人 这里就是现代诗歌的回响,比起艾略特的煤气工厂和负鼠脚作品,他们丰富,适合不同的主题,艾略特的作品我们可以剽窃艾略特,但总是和我们隔了一层什么东西。 哈代是我诗歌上的父亲,尽管我现在很少读他,这或许是因为他如此深入我心,我无需刻意为之。他去世了,他所生活其中并熟知的那个时代也已消逝了,我们已踏上另一条诗歌道路,但他对自然的谦逊态度,对受苦受难人们的同情,和控制节奏的分寸感一直对我们和当初一样受用。 我坠落,坠落到这里 到大西洋的雨里 飘零的模样像是 随风飞扬的谷粒 像眼泪般的,从高处 水珠落下指时针上 几乎弄脏了我的全身 被那些污迹 直到我感觉无用 成为被废弃了的一个 那时我想 我绝望地想 尽管不可见 他仍在那 可能在凝视 无论哪都好 不再帮助钟表匠人 测量并校准 但友善地对待我,让我 讲述我的手艺 ________ 相关阅读 圣-琼?佩斯:鲁滨孙的画像 曼德尔施塔姆:诗人与谁交谈? 索因卡:我曾看见它从灰烬中升起突现的云朵 罗伯特·潘·沃伦:诗歌就是生活 费尔南多·佩索阿:灵魂的无政府主义者 陈东飚译博尔赫斯诗歌总集之《圣马丁札记簿》① 陈东飚译博尔赫斯诗歌总集之《圣马丁札记簿》② 陈东飚译博尔赫斯诗歌总集之《创造者》① 陈东飚译博尔赫斯诗歌总集之《创造者》② 陈东飚译博尔赫斯诗歌总集之《创造者》③ 陈东飚译博尔赫斯诗歌总集之《创造者》④ 陈东飚译博尔赫斯诗歌总集之《创造者》⑤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uihaibaoa.com/hhbfzfs/6226.html
- 上一篇文章: 趣味野炊学当家参观模拟长见识记学
- 下一篇文章: 帝王蟹和海胆当零食,鱼子酱按公斤卖,狂野